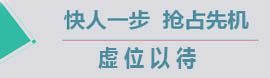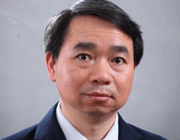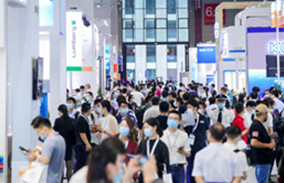【编者按】金国藩先生是我国工程科技界的杰出科学家,尤其对精密光学工程作出了突出贡献。最近出版的这本由金国藩口述、复旦大学教授张力奋撰写的《追光者:金国藩九十自述》,记录了金国藩先生的七十年科学实践和九十年人生体验。本文系该作序言,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转载,有删节。

《追光者:金国藩九十自述》
为金国藩先生撰写“自述”,采访断断续续,原计划两年完成,最后花了三年多时间。从他八十七岁,做到九十出头,让他等了。
科学圈外,听闻过金先生的人可能不多。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光学工程教授、中国计算全息技术和二元光学的开拓者。外界所知更少的,是他漫长的生命记忆、见证的时代。
我与金国藩先生相识,缘于金先生次子金纪湘。作为FT记者常驻北京时,我多次在席间听闻他家三代人与清华的缘份,心生好奇。
1909年,金国藩先生的父亲金涛,考取首届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当时报考条件颇为严苛,考生须“国文通达、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同行四十七人,有日后出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等。金涛前往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读土木工程,同学中则有后来更出名的胡适,读农学。因不喜欢农科,胡适读得痛苦,意志不上进,打牌上瘾消磨时间。胡适曾在日记中记载,一中国学长力劝他少打牌,后来终于收手。这个学长就是金涛,时任康奈尔中国同学会会长。学成归国后,他长期任铁路工程师,后在北大、清华任教。
吾友金纪湘是第三代,也毕业于清华,攻读计算机工程,后留美。2016年初,我回母校上海复旦任教,随口问纪湘,可否请他父亲做个口述史,对此我并不抱期望。过去多年,我至少动员过十多位老人,鼓动他们写自传或口述,但都碰壁。其中就有我的导师、前辈。最后他们都带着深埋、不愿触碰的记忆离世。每走一位,历史的残网就多一个窟窿。
没多久,纪湘转告,老爸听了我建议,愿意试试。这让我意外惊喜。第一次见面是2016年3月15日,我去了北京蓝旗营小区金先生家。最后一次访谈,是2019年12月27日,还是在他清华家中。据采访记录,面对面访谈共15次,平均每次3小时,计45小时。若加上电话,访谈应超过50小时。访谈多半在北京,有时借去北京开会、出差,挤时间谈一次。怕金先生着急,也常专程飞去北京采访。他好客,好几回访谈从家里聊到清华园外的餐馆。为不让我京沪两地奔波,他还两次到上海女儿家小住,以便我采访。我通常下午两点半到,怕影响他午睡。
正式采访前,先就金先生的履历做了功课,对重要的时间节点与事件,列了一百多个记忆的暗盒,等他打开。比如,他少年时代在北平的日常起居,就有近十个记忆点。每次访谈前,我都给金先生布置作业,他都事先认真做功课。
口述历史的传主,多半年迈,记忆遥远,细节更是茫然。金先生很耐心,对我各种角度的盘问,对细枝末节的核实,他从没表露出不耐烦。他的合作和放松,给了我更多信心与勇气。不过,他并非理想的口述史访谈对象,答问多半简约,有时短短几字,加上年代久远,回忆不及冰山半角。我不得不查阅更多资料,助他挖掘记忆和细节。他不热衷政治,骨子里逍遥。“文革”时,别人喊口号,他去颐和园昆明湖游泳。
我与金先生事先约定,这份自述可能公开出版。他说同意。我很怕“出版”两字会影响访谈的坦率与开放。如果不时闪出读者的窥视,采访很容易无意间背上一个牢笼。作为采访者,我只希望坐在背景里,这是金先生的人生。
每次访谈都整理成文字实录。三小时左右的对话,实录长达一万多字,时常涵盖大小近百个问题。访谈的另一个陷阱是,混乱的时空勾连。历史从来不是线性的,逻辑也很难干净。聊到尽兴处,金先生常常不经意话题一转,轻松跳越二十年岁月。我会聆听,把他悄悄拉回到约定的计划。有时金先生跟我搞拉锯战,不肯返回目的地,多个回合我才成功。拉他回来,是因为他还没交那堂课的作业。
身为首届中国工程院院士、前国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金先生在中国科学界,特别是光学界,为同行熟知。专业领域外,公众对他是陌生的,媒体报道也有限。遗憾的是,近年来对科学家的关注度越来越弱,媒体对科学报道无太强兴趣,科学传播与启蒙更是滞后。1915年,赵元任、杨铨等中国学人创办民间团体“中国科学社”,“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长达近半世纪,对启迪民智、启蒙科学、普及科学知识、培育科学素养影响极大。金涛先生当年也是学社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