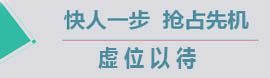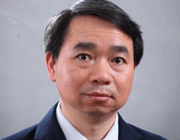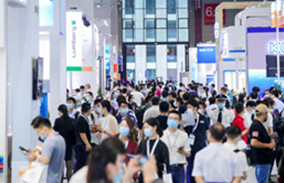编者按:
那是一个温暖的冬日下午,访问在金国藩院士家里进行。金院士的家在蓝旗营清华大学的宿舍楼。金院士接过张志刚教授手里的康乃馨,又递到夫人手里。夫人高兴地拿到阳台上,插到花瓶里。金院士的夫人喜爱花,从阳台到屋里摆满了花花草草,散发着清香。明媚的阳光透过阳台的窗户洒到屋里,把满满当当的客厅烘得暖洋洋的。
金院士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他和兄弟姐妹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上学时常常是学校放了暑假,紧接着“家教”开学,学古文、学英文、学算术……更重要的是,父亲那严格认真、一丝不苟的学风,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一生。
虽然出生于沈阳,但他2岁时就随父亲来到北京。从北京的育英中学转到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现河北北京中学),完成高中学业。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转入清华大学,工作迄今。曾任国家教育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亚太地区仪器与控制学会主席、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等。2002年、2005年连续两次当选为世界光学委员会(ICO)副主席。

金国藩院士
金国藩院士是我国光学信息处理的奠基人之一,在国内较早地开展了计算全息、光计算、二元光学(衍射光学)及体全息存储等课题研究。曾主持研制出我国第一台三座标光栅测量机,获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奖。获得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等。著有《计算机制全息图》、《二元光学》等。
金国藩院士接受了中国激光杂志社特邀编辑北京大学张志刚教授的采访,侃侃而谈他“转行”的研究经历,以及对国产光学仪器、光存储、光计算等技术的未来发展的看法。
我认识金院士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以后经常在各种会议上见到。最近一次相见是在2021年年初的一次评审会上。金院士虽然九十多岁了,精神矍铄,头脑清晰,十分健谈,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我先好奇地问了他怎么进的光学这一行。
张志刚:您在大学时,本来读的是其他专业,为什么后来又改去做光学?
金国藩:我这辈子改行多次,从机械制图到机械制造,从陀螺与导航仪器,最后到光学仪器。每回改行,几乎都是从头开始。
我原先入学北洋大学北平部,大二的时候(1947年8月),奉当时教育部的命令,北洋的北平部并入北京大学,我就进了北大工学院机械系。我上学的时候很多教师都是清华的,当时教授们比较清贫,大家都愿意有个“兼职”。那时候没有“专业”一说,学生随便选课,我当时什么课都选,内燃机、甚至化工系的几门课都选,就为了毕业之后好找工作。
毕业后,我在北大当了两年助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把北大和燕京大学的工科全部调整到了清华。当时清华的教师很少,他们看我在北大的时候已经帮着讲课,所以到清华之后仍然让我讲课,让我教画法几何和工程制图。之后,学校派我到哈工大学习了切削原理,回来以后我教了差不多有三四年。这期间,我开设了金属切削原理的实验,以及切削力、切削热、刀具磨损等实验,并制出我国第一台三向切削力测力仪。1960年左右,学校新成立了计算机系、自动化系、精仪系,还有核工业系等,将我调到了陀螺仪导航教研组,教航空仪表与钢外切。我当时不懂,就跑去北航听课,再回来教学生。现在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张孝文、周炳琨、王大中都是我的学生。
我还在清华机械系工厂供销科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做过一阵子工具车间主任。我把这段经历称为:“我是一块砖,哪儿需要往哪儿搬。”
因为我工作一直很努力,1965年的时候有一个出国的机会。当时出国只能去苏联或者东欧国家。但是因为我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有一个堂兄成分不太好,最终没能去成。再后来,领导安排我到上海外语学院学习,准备出国。但由于种种历史情况,我在那边待了三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把我调到光学仪器教研组当主任,任国防工办下达的“劈锥测量机”研制任务的课题负责人。这么着,我才跟“光学”沾上了边。
张志刚:您到清华初期,精仪系主要做哪些研究课题?